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阿斯利康骗保案”的定性争议
2025年12月19日,虞伟华先生(浙江高院原刑事法官)发表《阿斯利康骗保案恐怕是判错了》一文。指出相关案件中医药代表的行为不应认定为诈骗罪,而应依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评价为行政违法行为。就此,虞伟华先生在《准确区分医保欺诈与医保诈骗》《医保骗保典型案例分析四:本案应定性为医保欺诈,而不是诈骗罪》等多篇文章中,从刑法体系、行政法规范结构及刑事责任边界等多维度,进行了全面而严谨的论证。
无论是立足刑法谦抑性原则,主张严格区分“医保欺诈”与“医保诈骗”,还是围绕非法占有目的、刑法与行政法的边界,对既有判决展开反思等,这些文章在法理层面都展现出高度自洽性和逻辑严密性,值得借鉴和认真对待。
正是基于上述法理判断,在上文提及的刁留印案,一审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后,我们在二审接受委托,为其作无罪辩护。历经一年多的审理,二审法院虽作出改判,但仅将刑期减至5年6个月,案件定性并未改变。
由此,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法理上“是否应当如此”,与司法实践中“是否可能如此”,并不总是一致。在这种张力之中,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在现行司法解释已将相关行为纳入诈骗罪评价框架的前提下,辩护与裁判,究竟还能留下多大的空间?

从法理层面看,虞伟华先生系列文章所坚持的核心立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不能仅因“骗了医保”,就当然等同于诈骗犯罪。
文章反复指出,相关案件中医药代表的行为,发生在真实患者、真实疾病、真实用药需求的客观背景下,其所谓“造假”,针对的是医保报销的资格条件,而非虚构诊疗事实本身。这类行为,本质上更接近对医保管理规则的违规利用,而非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直接侵害。
进一步而言,从行为目的与利益流向看,行为人并非以非法占有医保基金为直接目的,其核心动机在于完成销售任务、获取佣金。医保基金的支出,系行为引发的后果,而非其主观上意图直接占有、控制和支配的对象。综合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主观恶性及整体社会危害性等因素,将此类行为定性为行政违法意义上的“医保欺诈”,在规范逻辑上更为周延,也更契合立法本意。
更重要的是,这种区分并非旨在“为违法行为开脱”,而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刑法作为最后手段,应在行政监管、行政处罚与行业治理足以发挥规制作用时保持克制。在此意义上,当行政法手段已能实现纠偏、惩戒与预防时,是否仍有必要动用最严厉的刑罚手段,确需审慎考量。
正因如此,上述观点在法理上成立,不仅具有充分的理论说服力,也值得司法实践借鉴与对照。然而,现实逻辑却“格外冷峻”。

当前,司法实践面对的“医保诈骗”问题,并非一张可自由裁量的“空白画布”,而是一套高度具体化的规范框架。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关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立法解释,以及2024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规范层面明确指向:只要行为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数额较大”等要素,即可纳入诈骗罪评价范围。
更关键的是,《指导意见》第五条、第六条,几乎将《条例》列举的主要违规情形,整体“刑法化”,纳入诈骗罪的规范评价体系。在此制度结构下,期待基层司法机关在具体个案中“跳出司法解释”,转而完全回归行政违法处理路径,以笔者愚见,很难。
这并非个别法官或检察官的主观选择,而是司法规范适用层级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司法解释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惯性”,当其与上位法存在张力甚至冲突时,实践中往往优先遵循司法解释。因此,在医保骗保案件中,只要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即便对其合理性存疑,也很难在个案裁判中直接排除适用。
理想固然重要,但终究无法脱离现实语境。对于医保骗保案件,“不构成犯罪”的法理论证,在当前制度环境下,尤其是2024年《指导意见》生效后,已很难转化为稳定、可预期的裁判结论。

在《指导意见》无法排除适用、司法实践倾向认定诈骗罪的前提下,需转向思考:如何在既定框架内,避免对医药公司相关人员作出机械、过度严厉的刑事处理。
在此层面,司法并非全无回旋空间。《指导意见》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实际上已经为“区别对待、区别处理”预留了接口。
(一)依法认定从犯,避免责任失衡
在阿斯利康骗保案中,还原行为链条可见:涉案患者均为真实肺癌患者,存在现实、迫切的用药需求;药品亦为真实抗癌药物。当时医保政策设置了严格门槛——基因检测阳性,而药价高昂,客观上使部分患者在“用药”与“经济承受”之间,陷入两难。
在此背景下,部分医药代表,应患者请求提供帮助,其行为虽违反医保规则,但在整个行为结构中,并非骗保模式的设计者或制度安排者,也非医保基金的最终占有者或支配者。相关医保基金并未进入其个人账户,其行为所指向的,是促成药品销售,满足患者用药,最终的直接受益者,仍是患者本人,而非个人非法获利。
从共犯理论看,刑事责任的认定,应当以行为人在整体犯罪结构中的职务层级、决策权限和实际作用为依据,而不能仅凭身份或结果作概括评价。对医药公司高管而言,只有在直接参与组织、策划骗保模式,或在公司层面作出明确决策并予以推动的情况下,方可认定为主犯。未参与组织、策划行为的,不应当然认定为主犯。一般管理人员亦同,仅因在岗位上知悉相关情况,或在职责范围内从事管理、协调工作的,均不能认定为主犯。至于基层员工,多处于执行层面,缺乏对行为模式的决定权,在主观恶性、行为地位及作用上,与组织、策划层级人员存在本质差异。依法将这类人员认定为从犯,既符合共犯责任分配原理,也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二)全面评价行为情节,避免标签化量刑
在量刑阶段,不能仅因“骗保”这一标签,就忽视案件的具体情节。
真实患者、真实疾病、真实用药需求,未诱发额外医疗资源浪费;医保基金损失相对可控,且多数案件中已全部追回——这些因素,均应成为判断社会危害性程度的重要依据,而非简单忽略。
尤其是,类似“泰瑞沙”这类靶向抗癌药,案件发生后,医保政策已调整,不再以基因检测阳性为唯一报销条件。这一政策变化,亦从侧面说明,相关案件所涉及的制度背景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整体危害程度,难与典型的职业骗保、恶意套现案件相提并论。
(三)适用认罪认罚与退赔,扩大缓刑空间
从已披露的大量案件看,多数被告人无抗拒调查、拒不退赔情形。相反,许多人是在企业考核压力、行业惯例与制度漏洞等多重作用下被裹挟,主观恶性与职业骗保人员存在明显差别。
在此情形下,若定罪后一概排除缓刑(或不起诉、免罚等)适用,甚至重判,不仅难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不利于刑罚教育、修复与预防功能的实现。
因此,在司法解释框架内,理应充分考量认罪认罚从宽、退赔退赃等情节,通过不起诉、免予刑罚或依法适用缓刑等方式,实现比例原则与个案正义的平衡。换言之,即便在诈骗罪的评价体系之中,司法实践仍然有空间作出更为克制、审慎的回应。

阿斯利康骗保案的争议,说到底,并非只是一个“有罪或无罪”的问题。它更像是一次现实检测:刑法的边界在哪里,司法解释能走多远,所谓的个案正义,还有没有空间?
法理上,严格区分“医保欺诈”与“医保诈骗”,坚持刑法的谦抑性,避免将行政违法刑事化,本有充分理由。这些道理,书本上写得很清楚,口号也喊得很响亮。但回归现实,在既有司法解释已经划定轨道的情况下,要求个案裁判完全绕开诈骗罪,不得不承认,几乎是一种奢望。
正是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辩护的重心,或许不是绕开规范本身,而是如何防止规范适用过重、过于机械。无法动摇规则,至少控制力度。依法认定从犯,完整评价情节,充分适用认罪认罚和退赔,合理拓展缓刑与免罚空间——这并非“网开一面”,而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为比例原则和个案正义留存空间。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理应严加保护。但刑法同样是最锋利的国家权力,锋利之物,用得太顺手,就容易伤及无辜。如何在打击恶意骗保的同时,不把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有限的行为一并碾压过去,考验的不是态度,而是司法理性与制度自信。
也许,在当下,这并不是一次裁判就能解决的问题。制度的惯性仍在,路径依赖还深。但至少,在每个具体案件中,应努力让刑罚不失必要性,也不超越边界。
这,或许正是面对类似案件时,较为务实、可行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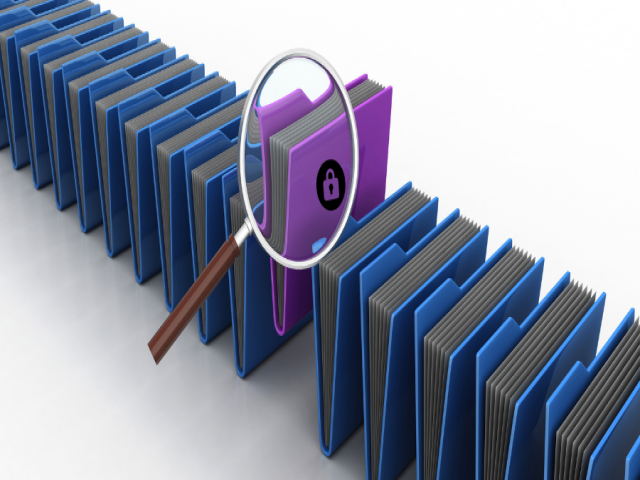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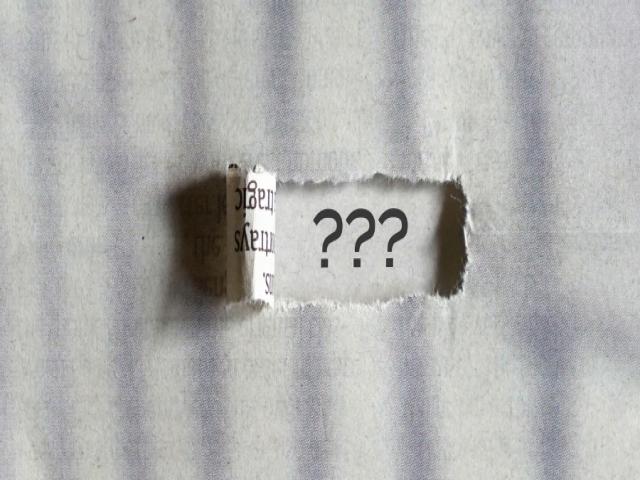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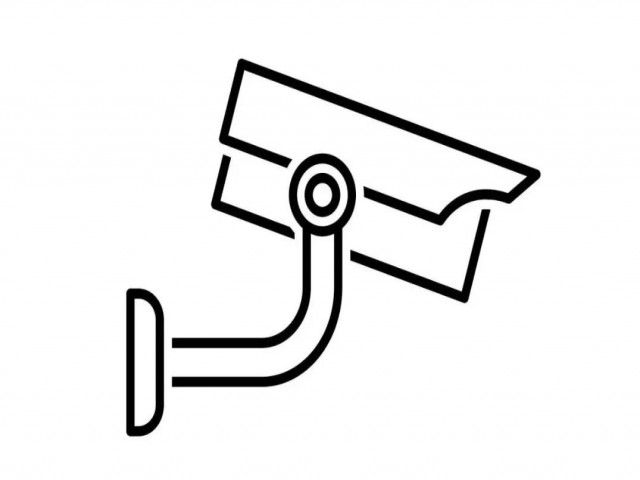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694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6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