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查中电子数据取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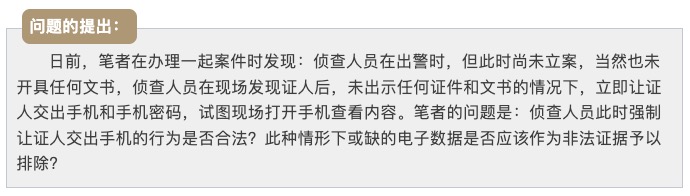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并不难,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地174条规定:调查核实过程中,公安机关可以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采取询问、查询、勘验、鉴定和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但是,不得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调查对象的财产,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本案属于立案前的调查核实阶段,根据上述规定,显然不能限制被调查对象的财产,也不得扣押被调查对象的财产。而且,本案当时的情形是侦查人员第一次出警,除了被害人的现场陈述外,没有其他任何证据,根据上述《规定》193条:公安机关侦查犯罪,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严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怀疑就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
实际上,本案的侦查人员在当时是在没有证据也没有任何法定手续的情况下对证人采取了侦查措施和扣押措施,属于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形。
众所周知,搜查、扣押电子数据是获取电子证据的重要方式,一般遵循“两步式”取证:首先,主要由侦查人员进入搜查场所,寻找证据并排除当事人对电子数据存储介质的占有;其次,针对存储介质内部的电子数据进行搜查。
侦查人员通常需要先行扣押电子设备,事后在实验室中电子数据进行映像复制,再借助专业取证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解析,最终获取介质内的电子数据。
在上述取证的过程中,扣押存储介质会侵犯当事人的财产权,而搜查个人信息则会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
而实际上,电子数据和存储介质本身在相关性、对应性和价值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如果在当事人的存储介质中存在海量电子数据,而仅仅有少量电子数据和本案相关,侦查人员在不了解的情况下,直接打开存储介质查看电子数据,显然会违反比例和最小影响原则。
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往往将电子数据依附于存储介质,并无精确的搜查对象和特定范围,而是发现后直接扣押整个介质,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证据取证规则》第十条 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电子数据,能够扣押原始存储介质的,应当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并制作笔录,记录原始存储介质的封存状态。
如此以来,电子数据相对于存储介质的独立价值被忽略,在取得介质后就自然而然的查看其中的电子数据也不认为此行为有违法之处。此行为实际上将“两步式”的取证直接变成“一步式”而且缺乏法律程序制约。
这种对电子数据的概括式搜查,实际上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过度干预,从而有违搜查、扣押对象特定性的要求。并且,随着电子设备的日常化应用,人们在手机中经常存储照片、视频等私密信息,这就使得存储介质中的个人信息面临侵犯隐私权的高度风险。
但,即便如此,通过上述方式扣押存储介质并获得的电子数据会有机会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么?
笔者注意到,我们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建立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因此,司法实践中,以严重违法法定程序,可能影响司法公正为由排除电子数据的案例几乎不存在。
在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时,法官排除电子数据作为定案根据的理由是电子数据不可靠、不真实,没有因为电子数据取证干预公民权利而排除电子数据的案例。
即使取证程序违法,如果能够补正或者解释,法官也往往以电子数据具有真实性为由,不予以排除。
广东高院在2014年的一起案例中,因侦查机关违法获取一部手机,该手机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其中存储的电子数据也间接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从该起案例可以看出,法官认为:电子证据是依附于存储介质而存在,无法适用独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实际上,我国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规则具有鲜明的真实性审查内容,换言之,合法性审查只是技术性规范而非权利保障规范。无论《刑诉法解释》还是《电子数据规定》,都只是停留在保障电子数据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层面,防止带案子数据因为侦查人员的取证活动而失真。
因此,可以说,电子数据合法性的审查判断本质上都是鉴真规则。即使法官认为电子数据“非法”,也是因为其不真实,而非取证行为干预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法理上说,制定排非规则的基础并非证据种类,而是要规制取证行为,只要取证行为干预了公民的合法权利且无合法授权,则应当对取证结果予以排除,尤其在一些大数据赋能侦查中,对公民权利的干预程度更深、隐蔽性更强。
![]()
刑诉法修订在即,笔者希望,能够在新的刑诉法中明确电子数据作为搜查的对象,一旦能够明确,类似本案的电子数据取证措施就不能在案件调查阶段使用,而只能在立案后使用。而且,最好能够明确,扣押存储介质和搜查其中的电子数据需要分别履行审批手续,并提供给辩护人。
而且,应当参考域外的有益经验,比如设定关键词、限制文件格式、检索文件名称等,限定搜查范围。即使侦查人员合法控制电子数据存储介质,也不能随意查看、复制其中的电子数据,应当符合比例和最下影响原则,防止不必要的干预公民权力。
最后,应当制定独立的电子证据合法性审查规范,而不是将合法性审查与真实性审查混合杂糅在一起。对于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取证,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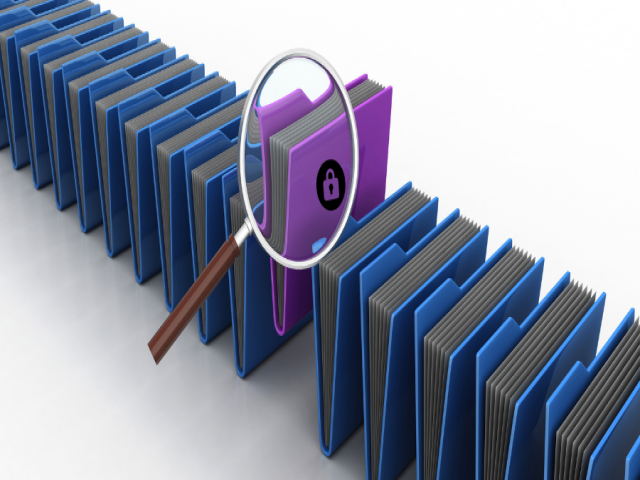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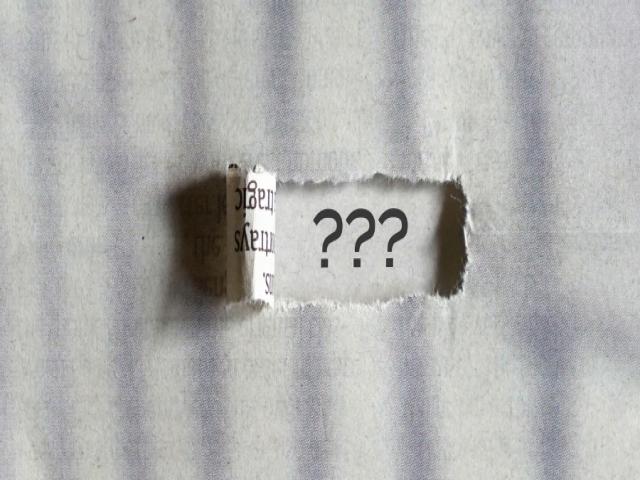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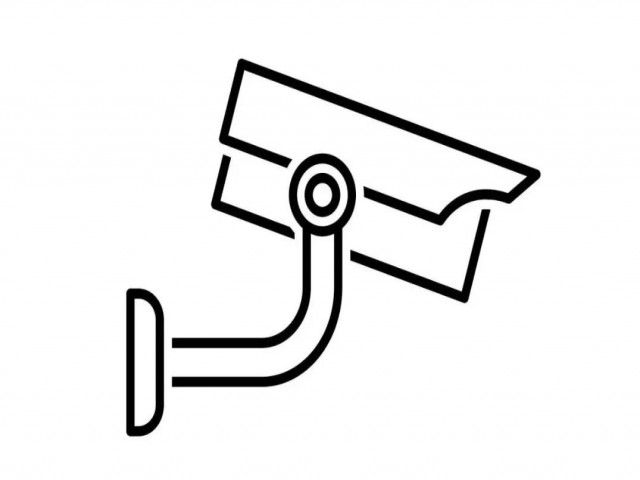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694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6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