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解释》对刑事辩护的影响-以同步录音录像为例
日前,号称史上条文最多的新刑诉法司法解释已经生效,实质修改的条文超过200条。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变化也会实质性的影响到刑事辩护。以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为例,令人遗憾的是,最高法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地位问题,甚至不如一些地方的规定明确。可以预见的是,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辩护人可能都无法查阅—更不用提复制—到同步录音录像,而卷宗中如果缺少了这一作为监督侦查机关非法取证的载体,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将被架空,刑讯逼供卷土重来也未可知。
先来看相关规定,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对作为证据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讯问录音录像,辩护律师申请查阅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解释第七十条条规定:依法应当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的案件,相关录音录像未随案移送,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人民检察院在指定时间内移送......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解释赋予了控方自主移送证据的权利,也就是说,只有控方将讯问录音录像作为证据材料移送法院的,辩护律师才有可能查阅到。如果不作为证据材料,辩护人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查阅。即使移送法院,辩护人也只能匆匆过目。事实上,在最高检已经明确表态讯问录音录像不是证据材料的情况下,不难想见,控方会有多大的动力将讯问录音录像作为证据材料移送。
而对于应当录音录像的案件,最高法依然没有树立必须移送的制度,而是规定“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检察院移送。但却回避了何谓“必要时”,将自由裁量权留给了法院。而且,即使法院认定情形必要,也只是“可以“通知,而不是“应当”通知,即使不通知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种只规定权利不规定责任的原则性规定,无论在刑诉法还是刑诉解释中比比皆是,而根据实践经验来看,这些规定除了成为法院不作为的借口外,不能起到任何作用。
然而,鉴于同步录音录像在防范冤假错案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回顾下同步录音录像的产生、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以期可以清楚地了解其将来的走向。
一、来处
同步录音录像始自2002年广东、浙江等地检察机关的自发性尝试,后逐步推广到全国。2005年,最高检制定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要求每次讯问都要全程录音录像。之后,该制度逐渐推广到公安机关侦查的一些案件中。2007年,两高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中规定,讯问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录音录像。2012年刑事诉讼法最终在立法层面将讯问录音录像确立为一项正式制度。
关于建立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目的,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可以管窥一二:“为从制度上防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了...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此解释表明,建立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目的,是“防止刑讯逼供”。这一点也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中得到了证实:“侦查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材料,主要是用于真实完整地记录讯问过程,在办案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供述取得合法性进行调查时证明讯问行为的合法性......用于证明讯问合法性的录音录像不作为证明案件事实事实的证据......”。
这一制度的出台,与当时严峻的刑讯逼供形势密不可分。但在很长时间内,对该行为治理力度不足,从2000年杜培武案开始,几乎每年都有重复上演的相似冤案及刑讯逼供问题。我们这么多年纠正的所有冤假错案无一例外都是由刑讯逼供造成的,这已严重危及到政法机关的合法、正当形象和民众对司法甚至国家的认同感。治理刑讯逼供成为恢复司法公信力的关键措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遂应运而生。
2017年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重复了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立场,第22条规定:辩方申请调取录音录像,“人民法院、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与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有关系,应当予以调取......”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官方仅仅将讯问录音录像作为证明取证合法的材料,限制了辩护律师使用讯问录音录像的机会。
但实际上,同步录音录像除了可以防止刑讯逼供外,还可以用来固定证据,防止翻供和诬告;还可以用作口供,具备实质性的证据功能。其不仅可以防范刑讯逼供,更可以审查取证过程中存在的引诱、欺骗等导致的虚假供述,从而更有效的防范冤假错案。
二、维谷
不可否认,同步录音录像在广泛推行后,在防范刑讯逼供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令人忧心:
第一、法律定位不清晰。全国人大法工委将同步录音录像仅作为证明取证合法的材料,最高检也在《关于辩护人要求查阅、复制讯问录音、录像如何处理的答复》中认为录音录像不是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而是属于案卷之外的其他与案件材料有关材料。而最高法在2013年的《关于辩护律师能否复制侦查机关讯问录像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录音录像已经作为证据材料向法院移送并在庭审中播放,不属于依法不能公开的材料。辩护律师要求复制有关录音录像资料的,应当允许。”可以看出,最高法曾倾向于承认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但在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录音录像法律属性的情况下,遗憾的是,因为两高的分歧,这次新解释的起草小组因为担心“录音录像中可能涉及到关联案件的犯罪线索、国家秘密、侦查秘密等,尤其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职务犯罪案件,较为敏感。如允许复制,在信息化时代,一旦传播到互联网中,可能带来重大国家安全和舆情隐患”,而做了“和稀泥”式的规定。个中原因与安徽吕先三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此不再赘述。
相较之下,一些地方倒是明确规定同步录音录像属于案卷材料。如广东省司法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实施办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案卷材料包括案件的诉讼文书、证据材料以及侦查阶段的同步录音录像和与该案件直接相关案件的案卷材料。
这种规定也应该推广到全国,赋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落实相关方的责任。
第二、控辩双方启动录音录像的权利严重失衡。如前所述,根据解释规定,控方不但享有决定是否移送同步录音录像的权利,也享有是否可以当庭播放录音录像的权利,对控方有利的可以当庭播放,不利的就可以以“不是证据材料”为由拒绝出示。有些地方的法检,甚至在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依然拒不移送同步录音录像而不担心承担任何后果。而辩方只有申请权,即使是面对应当录音录像的案件,法院也完全可以以不必要或者拒不通知检察院从而拒绝辩护人的申请。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根据本人的亲身体验得出的结论。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只能是空中建楼阁。
第三、实践中存在的其他问题。
首先,当下讯问笔录的制作过程存在很大问题,不少笔录并不能真正反映被告人供述的内容,侦查机关制作笔录时,会选择性摘录有利成案的供述,甚至篡改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真实意思以确保案件能顺利成案。在无法查阅同步录音录像的情况下,无论是法官还是辩护人,都缺乏判断庭前口供可信性的可靠手段,无法获得庭前口供笔录形成信息,难以判断庭前口供与庭审口供哪一个更可靠。一旦笔录真实性出现问题,出现“虚假印证”问题,错判在所难免,国内出现的冤假错案无不证实了这一点。
其次,据统计(蔡艺生:讯问录音录像证据运用的实证研究—以493份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证据科学 2020年第28卷),虽然2018年刑诉法123条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但是实际上,“应当型”案件的录音录像证据运用频率低。
此外,依据493份裁判文书载明的信息,公安机关及公诉机关随案移送讯问录音录像的共计21份,占比4.3%;若减去讯问录音录像刻盘附卷与载卷佐证的情况,则同步录音录像移送的文书仅12份,占比2.4%!无论是4.3%还是2.4%,这个占比可以说已经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新刑诉解释出台后,可以预见,这个比例会更低。
三、归处
我认为,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证据材料使用不存在任何障碍:首先,录音录像是侦查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获得的材料,具有合法性;其次,录音录像记录了讯问活动的全部过程事实,可以证明讯问过程的合法性,具有关联性;最后,录音录像一经录制完毕,便成为客观存在,可以被人感知,具有客观性。此外,根据《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相关规定,讯问笔录与讯问录音录像内容有重大实质性差异的,应当以讯问录音录像记录的内容(视听资料)为准。因此,同步录音录像不仅在在证明侦查机关是否刑讯逼供的过程中,具有独立的证据资格和直接证明力,在证明犯罪事实的过程中,虽然需要结合供述加以判断,也依然具有独立的证据资格。限制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会导致同步录音录像作为口供证明犯罪事实的功能大部分丧失,所谓防止侦查技巧或策略泄露的借口应当让位于查明事实。
更何况,当下的所谓侦查技巧普遍带有引诱或者欺骗的方法,据学者不完全统计,实践中出现引诱、欺骗等的案件占比超过30%(秦宗文:讯问录音录像的功能定位:从自律工具到最佳证据,法学家 2018年第5期)。而且,实践中,由于引诱和欺骗并非法定非法证据排除情形,法官往往对此类申请直接驳回,不在判决书中反映,因此,实际数据可能远高于上述数据。最高法也担心,如果这些讯问方法被认定为非法,会给侦查工作带来较大冲击,也从侧面反映了实务中引诱、欺骗方法存在的普遍性。而诱供发生的几率和危害与刑讯逼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更可能制造冤假错案。
因此,无论是防范刑讯逼供还是防止因引诱、欺骗等导致的虚假供述造成冤假错案,随案移送同步录音录像都是最优选择。
我坚信,作为文书记载科技进化的结果,同步录音录像可以视作被告人供述的有效替代,其证据属性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障碍,作为最佳证据证明案件实体事实的一天迟早会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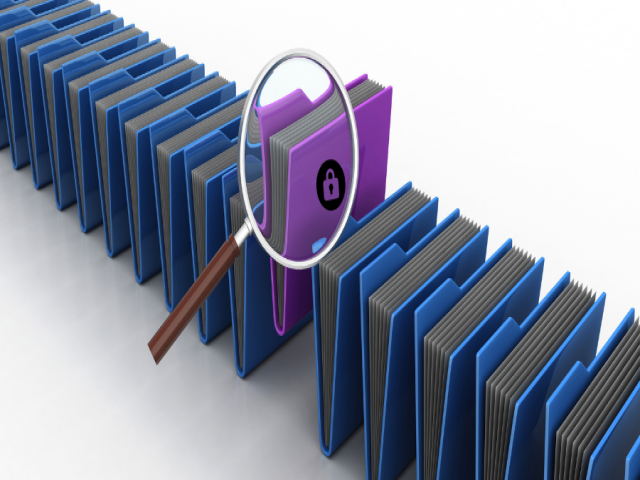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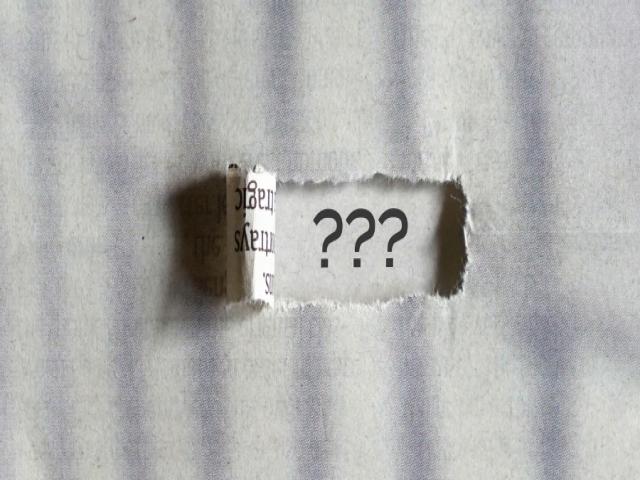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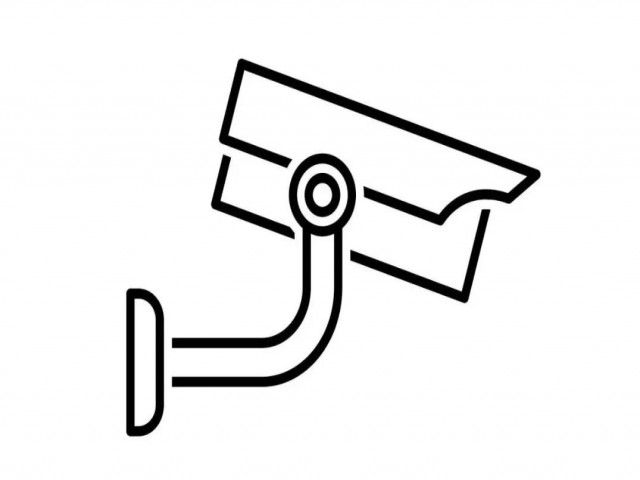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694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6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