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药监新规:从ESG供应链治理观察对链主药企监管力度的加强
接近2025年年底时,美国FDA向丹麦制药巨头诺和诺德(Novo Nordisk)旗下一处刚完成并购的美国制药厂发出警告函,函件直指该工厂在无菌药品生产过程中发现哺乳动物毛发污染问题及一连串不合规情况。FDA明确指出:即便诺和诺德的生产活动已经外包给该海外制药厂,但诺和诺德作为链主药企仍然对产品质量风险控制承担不可转移的最终责任。这一执法精神在制药行业引发了广泛讨论,这并非一次孤立的质量事件,而是一个愈发凸显的结构性风险——在高度外包化、并购频繁的制药产业环境中,链主药企是否具备对外包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治理能力。当生产被外包之后,责任是否也在事实上被“外包”了?
这一问题并非只存在于欧美市场,自中国在2019年全面推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制度以来,研发与生产逐步分离,药品的委托研发、委托生产迅速发展,将研发、生产等外包给受托研发/生产企业(CDMO)成为药企提升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路径。但在实践中监管者也逐步发现,一些药企在完成委托生产安排后,对生产活动的管理更多停留在签订外包委托合同(如《质量协议》)层面。对技术转移后的工艺稳定性、偏差调查质量、变更管理和现场质量体系运行情况缺乏主动、事前的合规管控动作。
在此背景下,国家药监部门于2026年1月发布了《关于加强药品受托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公告》,对药品受托生产的监管规则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强化。从新规的上下文来看,其关注重点并不在于“谁在生产”,而在于“谁在治理”。首先,新规试图解决的是 MAH与CDMO之间质量责任边界模糊的问题。监管不再满足于是否签署了质量协议,而是更加关注MAH是否建立了可验证、可追溯的管理机制,能够对偏差调查、CAPA落实、批次放行和变更控制进行有效监督。仅停留在合同书上的职责划分不再足够了,治理是否真实发生成为监管评判的重要依据。其次,新规显著强化了对技术转移和生产连续性风险的关注。无论是并购后整合CDMO,还是跨主体转产,监管都开始重点审视转移完成后一定周期内的质量稳定性,防止“技术交付即责任退出”的管理断层。这一要求,与诺和诺德案例中并购后质量体系整合不足所暴露的问题形成了清晰的呼应。再次,新规在监管逻辑上尝试问责前置。即便质量问题首先发生在受托供应商现场,监管部门也可能会进一步追溯链主药企是否建立了有效的风险识别和干预机制。如果链主药企未能证明其对外包生产实施了持续、实质性的管理,相关责任仍可能直接落在链主药企身上。这意味着,监管关注的重心正在从单一结果事件,转向对治理过程本身的审视。
在委托双方参与治理并承担各自职责的框架下,客观上也放大了药企自身的风险敞口。外包不再只是解决成本和效率层面的商业决策,而是一项高度依赖治理能力的合规决策。一旦CDMO出现质量问题,药企将同时承受监管处罚、供应中断以及由患者安全和治理失效引发的声誉风险。诺和诺德事件之所以具有标志意义,正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将目光从工厂现场,转向链主企业的整体治理能力。
因此,链主药企若仍然站在“合同委托方”的位置认为与CDMO签署了委托合同后就几乎切割了管理界面的话,将难以应对不断增强的责任要求。药企必须把 CDMO 当成自己内部工厂一样去管风险,可采取的行动是通过关键风险指标(KRI)融入集团治理结构中,将分散在项目经理、外包管理小组、质量部门专员的碎片化CDMO问题转化为可以被管理层(如董事会或风控委员会)识别和决策的风险信号。具体而言,将新规提及的核心风险敞口转化为“偏差发生频率及趋势”、“CAPA关闭水平”、“重复性问题发生率”这些可分析、可比较的风险指标,并形成向管理层定期汇报、横向比较的机制。当相关指标触及预警时,能够触发管理层层面的审议与干预,而不仅停留在项目层面。通过这种方式,转化对CDMO的角色认识,不再视其为普通供应商,将其质量稳定性与合规能力纳入链主药企整体治理半径之内,从而强化链主药企在外包生产中的“第一责任人”角色。
2026年药监新规并不是对CDMO模式的否定,而是对链主责任的一次重新校准。当生产被外包,治理是否仍然牢牢掌握在药企手中,正在成为监管与市场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对于药企而言,这既是一项合规挑战,也是一场关于治理能力和供应链责任的长期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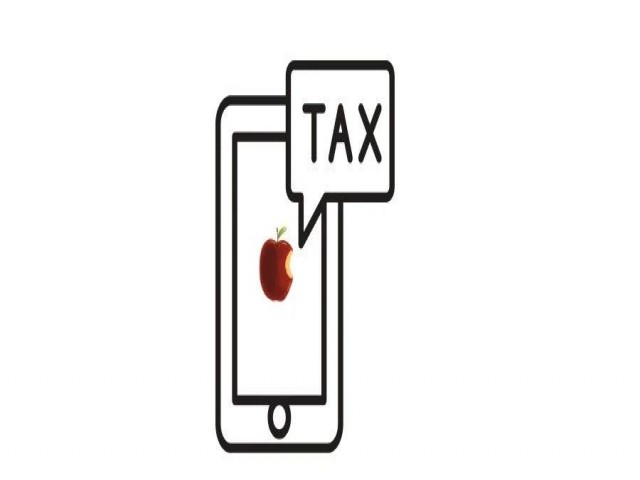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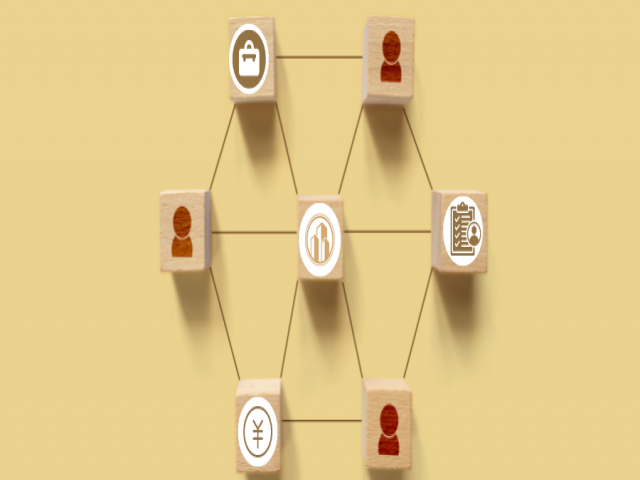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694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6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