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重拳出击,变成乱拳出击——再评“2025版知产刑案司法解释”
我们认为,新解释在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尤其是近年高发的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对于保障被告人辩护权、技术抗辩权、建立防冤机制方面,仍然付之阙如,未能兼顾技术中立原则,无法有效防范在未来的某些个案中,出现背离立法初衷,阻碍技术进步、限制公平竞争等次生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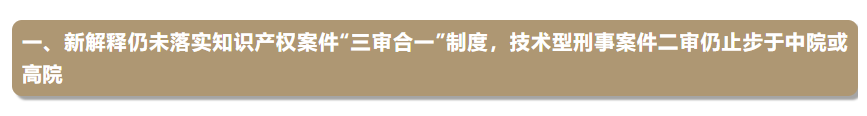
为了审慎查明技术事实、统一裁判尺度、杜绝地方保护,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在2016年11月4日就做出了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的重大决策,并发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明确要求: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审判“三审合一”,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2018年10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规定:“一、当事人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主要审理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第二条规定:“知识产权法庭审理下列上诉案件:(一)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授权确权行政上诉案件;(二)发明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属、侵权民事和行政上诉案件;(三)重大、复杂的实用新型专利、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权属、侵权民事和行政上诉案件;(四)垄断民事和行政上诉案件。知识产权法庭审理下列其他案件:(一)前款规定类型的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民事和行政案件;(二)对前款规定的第一审民事和行政案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依法申请再审、抗诉、再审等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三)前款规定的第一审民事和行政案件管辖权争议,行为保全裁定申请复议,罚款、拘留决定申请复议,报请延长审限等案件;(四)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知识产权法庭审理的其他案件。”
根据上述规定,知识产权案件,不仅要“三审合一”,而且,对涉及专业技术问题的民事案件,二审由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这明显有利于保障技术事实审查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涉及同样复杂技术问题、且直接关系企业命运与被告人自由的刑事案件,二审审理却止步于中院或高院,当事人不能直接上诉至最高法院。
对此,新解释未能作出制度回应,略表遗憾。在地方公安普遍强势的背景下,这种制度缺位,对于防范地方保护主义、“远洋捕捞”式趋利执法等问题,可能还会继续面临不少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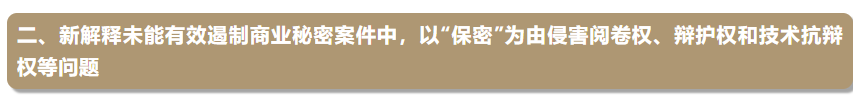
商业秘密案件为了防止“二次泄密”,可以采取不公开审理的方式,但绝不应以保密为由,层层设置障碍,侵害辩护人阅卷、鉴定、实质性技术抗辩等合法权利。
1.办案机关以防止“二次泄密”为由,限制辩方阅卷和技术抗辩,实质是“有罪推定”
遗憾的是,新解释仍延续旧解释,在第二十一条中规定:“应当根据案件情况采取组织诉讼参与人签署保密承诺书等必要的保密措施”,但何为必要的保密措施?这对保密范围、保密方式的界定模糊不清,给予办案机关过于宽泛的授权。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往往被滥用,甚至演变为剥夺辩方阅卷权、技术抗辩权的工具。例如,某地检察院发布的《防止次生伤害,三分院保护商业秘密有高招!》中,规定即便律师签署了《保密承诺书》,但也只能阅看、摘抄涉密材料,而不得复制,甚至摘抄件也要留存检察院办案部门,不得带走。浙江、江苏部分地区亦有类似做法,更有甚者,干脆连询问、讯问笔录、鉴定报告也认定为涉密材料,禁止律师复制。
考虑到商业秘密案件中,涉案材料动辄成千上万页,此类限制实际上堵死了通过鉴定、引入技术专家进行实质性技术抗辩的路径。“保密措施”异化为对辩方权利的剥夺,控辩双方权利严重失衡,极易引发冤假错案。
以防止二次泄密为由,限制阅卷和技术抗辩,明显违反《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关于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规定,也违背第三十九条第四款关于辩护律师可以向被告人核实证据的规定。本质上,这种限制体现了办案机关的“有罪推定”。 在未经辩护人实质抗辩(确实存在辩护人作有效的技术抗辩后,司法机关否定商业秘密的情形)、法院审查之前,便默认权利人所指称的技术信息已构成商业秘密,实质上是控方“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严重违背了审判终局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
2.限制阅卷和技术抗辩,导致证明标准“民刑倒挂”
更进一步,这种做法还导致了证明标准的“民刑倒挂”。民事诉讼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刑事诉讼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在民事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2526号判决中指出:“权利人提供了证明技术信息秘密性的初步证据,或对其主张的技术秘密之“不为公众所知悉”作出合理的解释或说明,即可初步认定秘密性成立。权利人初步举证后,即由被诉侵权人承担所涉技术秘密属于公知信息的举证责任,其亦可主张将公知信息从权利人主张范围中剔除,从而在当事人的诉辩对抗中完成涉案技术秘密信息事实认定。”即明确鼓励通过双方的技术对抗,完成对商业秘密事实的查明。权利人仅需提供初步证据后,被诉方仍可通过举证质疑,将公知信息剔除出权利人主张的秘密范围。民事诉讼尚且如此,刑事程序不应背道而驰,更应保障辩方通过全面阅卷、技术抗辩来完成技术秘密事实的认定,从而避免冤假错案发生。
3.限制阅卷和技术抗辩,可能被恶意滥用,导致背离保护创新的立法初衷
限制阅卷和技术抗辩,可能被人恶意利用,制造冤假错案,阻碍技术进步。司法人员并非特定领域的技术专家,如果不允许辩方全面阅卷(尤其是不允许复制)进行实质技术抗辩,无法防止有人滥用程序,将公知技术包装成自己的商业秘密,或将他人的创新技术比对成与自己的落后技术相同(反正辩方拿不到自己的技术,百口莫辩),恶意打击竞争对手的合法创新,限制科技人才的正常流动,扼杀创新活力,最终背离保护商业秘密、促进创新的立法初衷。
4.建议以“双向承诺”代替“单向限制”
因此,建议以“双向承诺”机制代替当前的单向限制。当前,办案机关设置诸多障碍,限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拿到作为核心证据的商业秘密载体或鉴定报告,要求签署“承诺书”承诺不能给任何第三方(包括鉴定和引入技术专家抗辩),这是单向的承诺书,只约束被告方,但对权利人该如何诚信、正当行使诉讼权利则毫无约束。鉴于商业秘密案件的发起人一般都是内心确信被告方已接触、知晓其所声称的商业秘密,方可发起报案/起诉,司法机关可以要求权利人签署“承诺书”,承诺其确信被告已知晓涉案商业秘密,并同意将相关证据完整交付给辩方进行质证。
唯有通过“双向承诺”,才能有效避免各种“顾虑”,使当事人能够进行实质性技术抗辩,也更有利于法院、检察院查清案件事实,减少冤假错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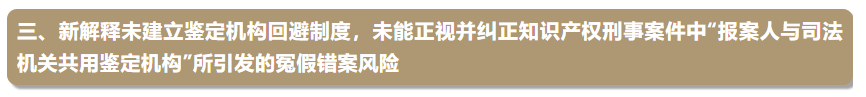
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陋习:由报案人付费,司法机关出面委托报案人此前已聘请过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甚至直接使用报案人提供的鉴定报告作为定案依据。
这种做法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严重破坏了鉴定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在此情形下,相关鉴定人和鉴定机构,依法应当回避。《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条规定:司法鉴定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诉讼当事人、鉴定事项涉及的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其独立、客观、公正进行鉴定的,应当回避。司法鉴定人曾经参加过同一鉴定事项鉴定的,或者曾经作为专家提供过咨询意见的,或者曾被聘请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过同一鉴定事项法庭质证的,应当回避。
遗憾的是,新解释未能设立针对鉴定机构的回避机制,也未明确禁止此类利益冲突的鉴定安排,未能有效回应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道德风险与程序失衡问题,留下了重大隐患。
如果继续允许报案人、侦查机关与同一鉴定机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不仅容易形成控方主导、鉴定机构配合的事实认定模式,也将使案件审理陷入“有罪推定”的误区中,严重侵蚀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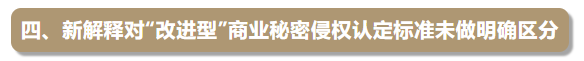
民事司法解释在认定商业秘密侵权时,将标准从“实质相同”进一步拓展至“改进”,边界模糊不清,刑事司法“萧规曹随”,亦未作出合理限制,存在明显失衡。
商业秘密侵权的技术比对,应严格回归技术事实,以技术特征的相同或整体实质相同作为判断标准,而不能含糊其辞,将所谓的“改进”也纳入侵权范畴。尤其要强调的是,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获取、披露行为,本身可以单独处罚,不能因为获取、披露成立,就无原则地扩大使用商业秘密行为的打击范围。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对原有技术的“改进”,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优化性改进”,在于克服原技术固有的缺陷;二是“适应性改进”,在于配合自身不同型号等的生产需求而进行调整;三是“颠覆性改进”,即改进本身具有创造性,达到独立创新的程度。这三种改进方式的创造性高度差异极大,但在当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不加区分,“毒树之花开出的毒树之果”皆为“有罪”,一律将上述各种“改进”认定为对原有技术的侵害,仅在设计思路根本不同的情形下,才予以排除。这种“一刀切”的认定模式,实际上将刑事责任范围大幅扩张,极易导致过度打击。
专利制度是以“公开换保护”,从而推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专利的授权还需要经过专利局的严格审查。而商业秘密的保护则与之相反,依赖于秘而不宣、由权利人自行(通过鉴定)归纳密点。在这种极具弹性的保护机制下,如果一方面降低密点认定的创造性标准,另一方面又将“等同”和“改进”也纳入保护范围,实际上会使商业秘密的取得门槛低于专利,但保护范围却大于专利。这种保护失衡,不仅背离了鼓励竞争与创新的立法初衷,也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合理预期,甚至可能反向阻碍技术进步。
因此,商业秘密侵权认定的基本规则,应当严格限于“实质相同”,不应借由“改进”这一模糊概念,将标准从“实质相同”扩展到“相关”。否则,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将异化为技术发展的禁区,成为权利人封锁技术进步的工具,形成事实上的过度垄断,严重违背竞争与创新并重的法律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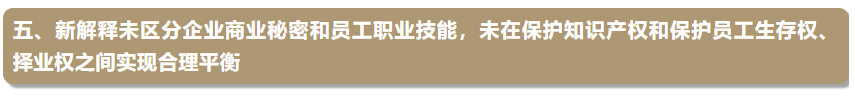
实践中,大多数商业秘密案件源于员工跳槽。
对于如何区分企业商业秘密与员工通过劳动积累形成的职业技能,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与保障员工生存权之间实现合理平衡,新解释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缺失。
对于员工偷走雇主商业机密并非法获利的行为,当然需要打击,但是,我们也必须警惕,有的企业对跳槽或自主创业的员工,动辄启动侵犯知识产权(尤其是商业秘密)刑事控告,如果司法机关把握不当,或是趋利执法、办人情案,而防冤机制又不健全,就可能严重挤压人才自由流动的空间,变相垄断员工择业权甚至人身权,最终是以“保护创新”为名,行阻碍创新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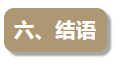
创意之火加上利益之油,是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石。
运动之火加上腐败之油,则历来成为冤假错案的温床。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的真谛,无外乎是举国家之力“保护创意“与“平衡利益”,而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防冤机制,则是题中应有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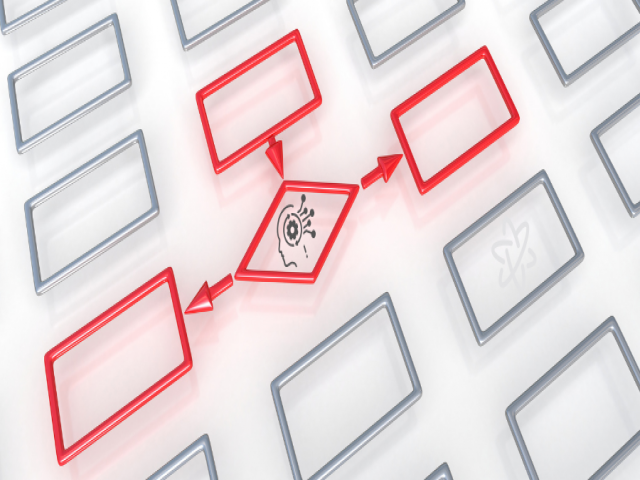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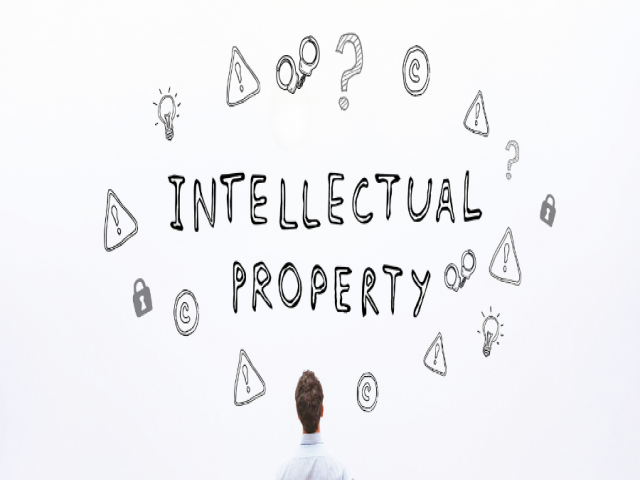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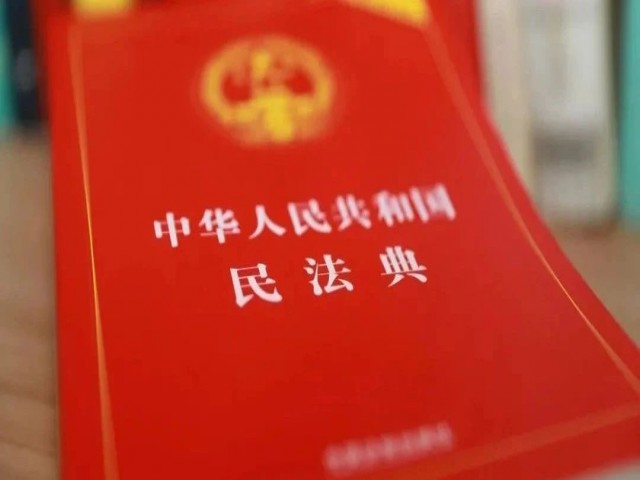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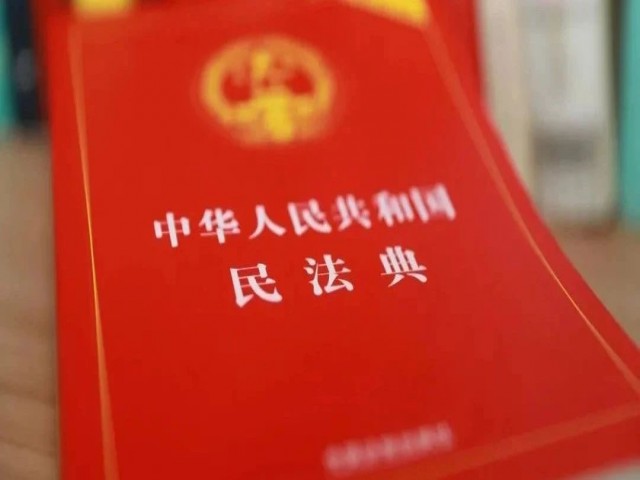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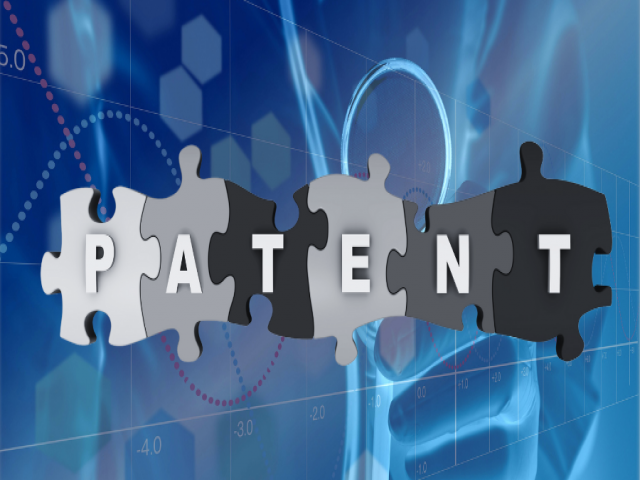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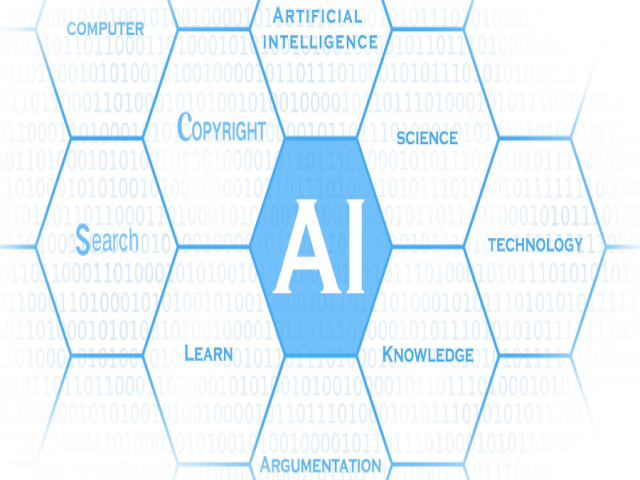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694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694号